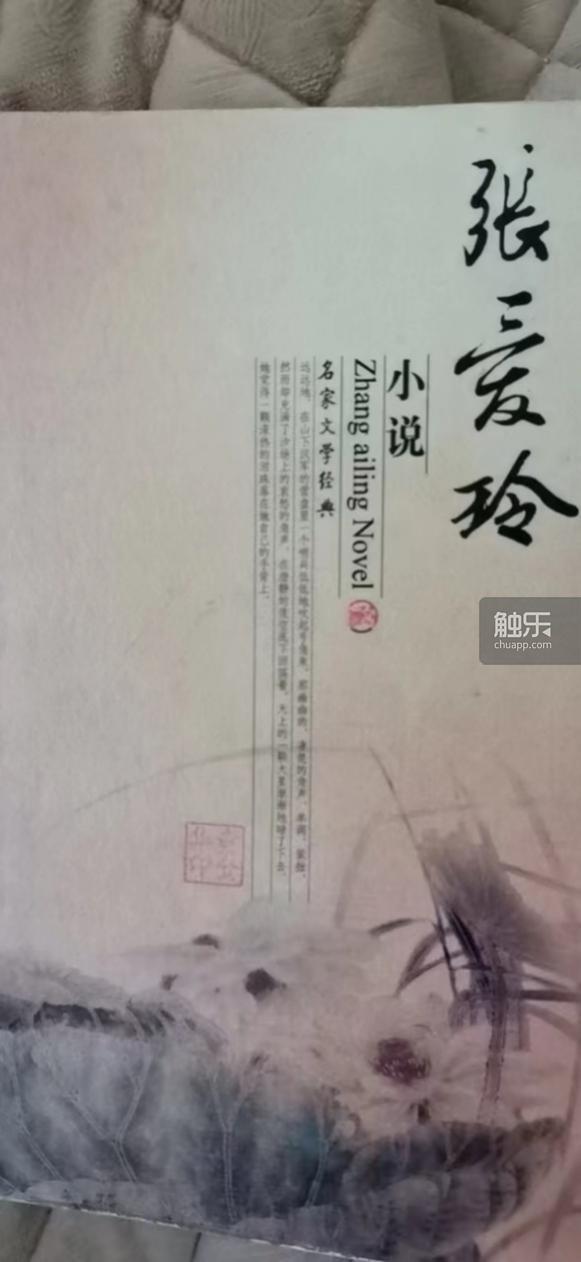我喜欢这样的收梢。

因为准备到北边过春节,周末坐动车去了一趟省会,收拾要带走的衣服和书本。书很多——大部分是小说和笔记,在我回程的路上,那些小说就这么堆在我面前,每本都被泪水和汗水弄得皱巴巴的,我伸出手拿过一本,随意地翻页。
我拿的小说叫《在切瑟尔海滩上》。这部小说以一次性事不遂为切入口,讲了一对1961年刚刚完婚的夫妻无法用言语沟通,甚至不能说出最简单的性欲,引发了许多误解的故事。
这本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去年的5月份,我把它丢进书包,背包去另外一个城市见喜欢的人,春天末尾的整整5天,我们都待在不见天日的海边旅店中,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而昏暗不透光的窗帘下,在亲吻中,我的血流在肌肤下微微跳动,上涌,像春花一样绽放。在车上,我抚摸着书脊,人依然凝滞在那一刻,因为它甚于任何感觉,哪怕是耳后爆炸,长矛穿腹,或者灵魂折磨,尽管这些我一样都没感受过,那么就甚于想到这些的时候的感受吧。

一边寻找着当时的感觉,我一边把小说快速翻到了底页,那儿有一道狭长的口子,口子周围因为吸了水,变得很硬。春夏之交的那几天,我一直在看这本小说,快到结尾的时候,我似乎和她爆发了一场争吵。我睁开眼,她已经走了。夏天的滞重感在我周围弥漫,我由此凄凄惨惨,展开小说,想要看完,却只能徒劳地任由目光滑过一行行字句,怎么都看不下去,等我放弃的时候,手里的那页已经被我捏成了两半。
在小说里夹着的读书笔记里,曾经的我写道:在亲密关系中——如挚友、家人、爱人——我们心中的某一部分强烈抗拒用显式语言表达这段关系应该说出的话语。当我们想要表达赤胆忠诚和心意相通时,我们更倾向于用行动来表达——我们一起吃饭、相互拥抱、如影随形。
我盯着自己的字迹,任由思绪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过去的思考中。
如果把这些行动换成话语呢?“我承诺效忠于你”,这是表达你与部落或民族同心同德。“我对信条忠诚不移”,这是表达你对信仰的坚定。“我爱你”是想邀请另一方回复“我爱你”。这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在完成仪规。
你不会说:“让我们彼此相爱。你病痛时我照料你,我病痛时你扶持我。以后的家务我来承担,钱我来赚,每周我们做很多次爱。”。似乎我们都认为,如此说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亲密关系应该说出怎样的话语,想必是因为显性语言系统控制着谈话,与大脑的理性、审慎、意识部分相关联。
但如果你表达出这是由某些深层、原始的情感所控制,你就有理由让对方相信这个承诺由心而发,相信你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转眼就跑到门外。所以,要如何让对方知道你的话是出于激情——而非理性的考量呢?
我合上小说,放回去。尽管过去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我所面临、思考的问题依旧没有答案。随着列车行驶时的微微颤动声,我想要试着再找一次答案。
“我爱你。”想象中的我说。然后我又说了一遍,发出了一点呼气和吸气的声音,然后又一遍,又一遍,直到我那残留下来的最后一点自我意识,以及照这模式说话的愚蠢的感觉,也都消失殆尽,好像生活里或者电影里都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似的——我再一次张开嘴,终于声音从胸腔中慢慢升腾而起,空气在振动,我大声说了一个词,但是正好被列车到站的播报盖过去了。
我轻轻叹气。目光扫过更多堆在上层的小说,我看见了《甜牙》。在《甜牙》的结尾,汤姆请求塞丽娜成为他小说的合伙人。
在我的笔记里,合伙人这个词被打上了横杠。
“我要像汤姆一样。”我规规矩矩地写道。
“原谅我,我想要……不,我必须。”——这是小说的原文,我也一并照抄在了笔记里。“尝试你的孤独,代入你的不安全感、对于爸妈和睦的渴望、家人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兼顾,代入你那不时流露的一点点探询、一点点无知、一点点执著和一点点社会良知,代入你那些自哀自怜的时刻和遇事大多循规蹈矩的习惯。与此同时,没有忽略你的聪明、美丽和温柔,没有忽略你热衷睡觉也喜欢玩乐,没有忽略你的幽默和那种老是想保护别人的本能。”
这些字迹让我觉得很陌生,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去年的自己。去年过去得如此之快,以至年终总结在这么一个周末、在列车上悄然来临。
被塞到《甜牙》下面的一本小说是《赎罪》,《赎罪》下面是一连串俄罗斯小说,那是年底在大学旁听的时候,教授布置的参考书目。以及,我没有错过那本布满灰尘,从垃圾桶底部打捞出来的张爱玲的小说集。里面有一篇讲霸王别姬故事的小说我还记得。
在那个故事里,虞姬杀死自己前,给项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以这次夜话作为对过去一年的收梢,我觉得也还不错。